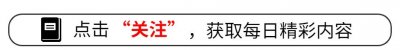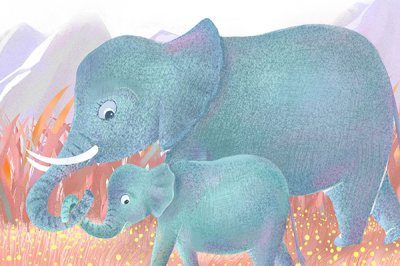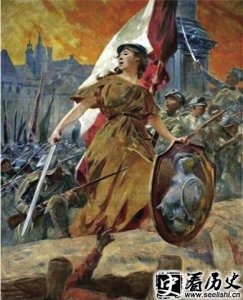行走的历史:召稼楼古镇

“召稼楼”这个名字有些文气也有些土气,望文生义感觉有 “召唤农民从事稼穑”之意,查考一下关于有关该古镇的介绍,果然名达其意。据记载,北宋时期召稼楼所在的地方还是滨海滩涂,距离大海很近。南宋时期随着重心南移,中原地区人口大量南迁,一部分人便聚集到了这片荒滩。当时寓居此地的谈德中在此建一小楼,广泛召集稼耕农夫垦荒种田,“召稼楼”因此而得名。后来随着垦荒的不断推进和人口不断集中,也吸引了商贩、士绅和文人前来,沿当地的夹河而居,遂城繁华集镇,延续至今。历经漫长岁月的冲刷,大海已经被沉积的泥沙推向远方,数十代人不停歇的脚步,已经将昔日的滩涂踏成坚实的土地,不同时代层垒叠砌的建筑,创造着历史又掩盖了历史,唯有穿镇而过的河流,静静地流淌着,见证了岁月的沧桑变幻。

如今,召稼楼仍然是一座“活”的市镇,信步其间,浓浓的烟火气和浓郁的乡土气扑面而来。这里似乎是猪肉皮的交易集散地,到处都可以看到经营猪肉皮的店铺以及储存猪肉皮批发的仓库,猪肉皮就装在透明的简易塑料袋中,随意地堆积在一起,马路上,装载着成袋猪肉皮的卡车忙进忙出,很难想象人们经手的是可以吃的食物。
店铺的招牌上有正宗三林塘肉皮,也有猪冠军现做肉皮,广告都稍显夸张,似乎猪皮是人间至美之味:“选料精良、营养美味、无任何添加剂,选用云南散养黑猪皮,炒出肉皮为金黄色,其口感酥松、润滑、尤其是那海绵般的孔洞,不仅弹性十足,还很有嚼劲,也最易吸味,就是所谓上海人口中所说的入口一包汤。”记得猪皮做成的鲜汤或素炒过去是上海人餐桌上的常客,现在似乎已经不那么流行了,但这种上海人的传统味道显然还在古镇及其周边延续着。除了上海人记忆深刻的猪皮外,这里还汇聚了各地的传统美味,安徽的烤鹅,各地的酱菜、南汇咸肉、苏记咸蹄等等,咸货腌货居多。用盐腌制生鲜食材,过去是一种储存保鲜的方式,现在则成了一种传统的味道记忆,没有咸货宴席就缺少了主料,过年就失去了味道。

穿行在狭窄的古镇小巷中,各种生鲜、腌制、烹饪的味道杂混着,一起冲入鼻中、口中,像一锅浓郁粘稠的汤汁,无处可躲。街边的一些小饭店都不怎么起眼,但橱窗上贴出的本帮“老八样”图片颇能吸人眼球:本帮扣三丝、本帮扣咸肉、本帮扣蛋卷、桂花肉、本帮蒸三鲜、金针木耳鱼、本帮三鲜肉皮、梅菜扣肉。老八样是各种传统食材幻化成佳肴的结晶,经历了漫长岁月逐渐被人们认可,成为婚丧嫁娶过年过节宴席的必备菜肴。这些菜品一旦成型就逐渐被仪式化,而具有了传统、礼俗和财富象征的意味,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尽管老八样菜品都标以“本帮”字样,但这里作为各地移民汇聚之地,也一定是各地风味经过交错、冲突、选择、淘汰,最终整合凝练而成。

没有考察古镇的刻意,也没有参观的事先规划,只是随意到此闲逛散心。事后了解到这里有名的古迹有礼园、梅园、奚氏宁俭堂宅院、奚家恭寿堂住宅、礼耕堂、奚世瑜住宅,而且这里还是上海城隍秦裕伯的故里。但这些古迹似乎都被我们完美地错过了,要么这些古迹都不在古镇步道显眼的位置,要么就是我们匆匆而过未加留意。
只有两处印象颇深。一处是广智学堂旧址,这里虽然有个很气派的门楼,但一看就是新建的,缺少应有的古气,门内其实是现代化的碧丽宫大酒店。门外墙上的人物像和说明倒是将一此旧址和一些熟知的著名人物联系在一起。据记载,该学堂历经元明三代,由当地望族奚氏所建,广招名师而闻名浦东,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张闻天、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以及曾任北洋政府总长,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事件的人物之一曹汝霖,均曾在该学堂接受启蒙教育,然后奔赴各地,影响了历史而任后人褒贬。

另一处是“资训堂”,即奚氏的宅邸,始建于清代,数次改建,最终受外来文化影响,形成中西合璧的样式。如今大部分建筑已经毁损或重建,独存西洋门楼及围墙的残垣,其残破却靓丽的色彩,见证了中国上海近代化的历程。

离开古镇的时候,忍不住买了几只街边小摊的“油墩子”。不知“油墩子”是不是上海独有的小吃,但名字一定是上海的。到上海读大学之前没有在家乡见过,此后在全国各地似乎也没有看到过。“油墩子”是我们80年代在沪读大学的学生们的集体记忆,那时,在摊贩经济盛行的年代,大学门口总是有这样的“油墩子”小摊,一位大妈,一盆面糊,一筐萝卜丝,一口油锅,萝卜丝裹上面粉在油锅里炸至焦黄,里面吸满了油。一只下肚,营养不良的肚子立刻充满了油水,那份满足感现在似乎很难体验到了。

古镇已经贴出通告,说2023年起古镇进行封闭改造,不知改造后会更好还是更糟,到时候再一探究竟,也设法寻找一下那些错过的著名古迹遗址,稍稍弥补一下留下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