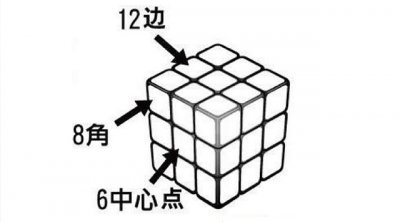每晚女友想亲热时我就拿杂志上厕所,这天她听到奇怪的声音
朱妮涂了黑色指甲油的手,动不动就拨弄一下头发。

我对她的挑逗视而不见。我在看电视,全神贯注。朱妮本来坐在阳台上,她只好走过来,拖鞋在地板上蹭出沙沙的响声,而我,总是在声音响到脑后的前一秒站起来,拿一本杂志,进了卫生间。
认识朱妮是在一年前的一个酒会上,朱妮并不在来宾名单当中,她是一个负责演奏的学生带来的。
酒会后,我就对朱妮展开了热烈追求,直到她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并且搬到我家来为止。
朱妮是美的,她的美过于刺眼,就是你可以把她带出门交际,但时时担心她会惹祸的那种女人。
杨玉在外贸大厦门口等我,看到我的车,便扬起笑脸,扑了过来。
杨玉是我最近结识的姑娘,比我小五岁,比朱妮大三岁。在有些人看来,她和朱妮叫板,真是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她并不那么美,而且纯朴得过头了。可是我要说,给出这样评价的人,他们根本不懂得女人。
女人最重要的不是美貌,而是除了你,她心里没有别的男人,眼里没有别的风景,她每次等你等到脚断也没有怨言,你要为她买衣服时她会紧张地摆手说,不要不要,然而每次约会都穿上它。这样的姑娘真的很好,她越是不要你的什么,你就越是想把全世界都给她。
换成朱妮,你只需让她不化妆出门,她就会死的。
我是一个年近三十,有点小事业,有点小疲倦,想要成家的男人。所以我知道朱妮不是我的理想,从一开始就知道,却并不妨碍我顺水推舟地把她哄上了床。
这天我带杨玉去买了一条碎花长裙,我在橱窗外一眼就看中了它,素淡的花色,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杨玉的裙子,只有安静纯朴的她,才配穿安静纯朴的它。
我不能直接把朱妮赶走,当初是我力邀她来的,所以这么没风度的事,我做不出来。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碰她。我想以她的聪明,要不了多久就会知趣离开。
每到夜晚,我就拿本杂志上厕所,眼睛盯着杂志,耳朵里听着朱妮的拖鞋,在客厅地板上走来走去,沙沙作响。
我就在这时做了一个决定,把卫生间的门开了一条缝。
我背对着门,杂志翻到模特衣服穿得最少的那一页,当第一声呻吟从我喉间发出时,我确信外屋的拖鞋声戛然而止。
我想我要是朱妮,就会不顾一切地冲进来,一把撕碎那本杂志,然后愤怒地问我,为什么宁愿自己解决也不愿意碰我?
但是外面很安静,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这天我去其他公司考察业务,出门的时候,却看见马路对面一台单车后座,搭着我那纯朴的姑娘。
我的视力很好,尽管隔着一条马路,我仍然清晰地看到杨玉飞扬的笑,和与我在一起时迎合的笑,很不同。
那是一张充满爱情的脸,爱是从骨头里漫出来的。你稍微活一点岁数就会明白,女人的爱情,不是你给她全世界就能换来的。
回家时我以为会迎来朱妮打好包的行李。因为在洗手间上演的戏码,我已经连续演了一星期,我有些厌了,我想她也厌了。
可是朱妮没有走,她正在厨房奋力剁着一块大排骨,身上穿了一条碎花长裙。
她的碎花长裙,和我买给杨玉的碎花长裙,是一模一样的,一样的花色,一样的牌子。
她必定每天尾随着我,看我和那个纯朴的姑娘,进出商场,酒店,饭馆。我无法想象她的表情,只知道,她从来都不声张,每天猫一样安静地待在屋子里。
我的理智还来不及滚过脑子,就已经冲着朱妮失控地大叫:“脱下来!你给我脱下来!”
朱妮走了, 她根本不喜欢素淡风格,却徒劳地想要模仿那个让我迷恋的姑娘,可惜她的风情出卖了她,黑色指甲油出卖了她,朱妮就是朱妮,不可能变成别人。
四个月后我在一幢即将要拆迁的旧楼里邂逅了朱妮。我是来与住户洽谈拆迁条件的,而朱妮就混在躁动的人群里。
我一直都不知道,她是在这个破旧的居民区长大的,她的母亲直到现在还住在这里。其实我几乎不知道她的任何事,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交过几个男朋友。
我只是习惯用男人的思维,来看待她这样的女人。
再次见到她,我才发现原来我很怀念她。
第二天我去找她,可是她已经带着母亲迅速搬走了,没有申请什么补偿。
那幢旧楼于三个星期后拆除。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朱妮。
我到现在还在想念她,不管你相不相信。
我身边依然徘徊着杨玉那样的女子,可是关于女人的赏鉴理论,我已经知道那是狗屁,所以不再说给任何人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