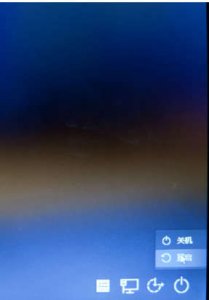瞿秋白纪念馆观后感的简单介绍
原载《党史文苑》2017年6期
十月革命后蒋介石奉命考察苏俄纪略
张家康
十月革命胜利,列宁创建的苏维埃政权还处在西方世界的诅咒和包围之中,根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唯此,列宁派出使者游说各国,以期国际社会的承认。孙中山在领导国民革命中四处碰壁,而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和苏俄愿意施以援手的允诺,使孙中山看到了革命胜利的曙光。正是在此背景下,孙中山才组成以自己姓名命名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赴苏俄考察十月革命的真实的情况,团长选择的是年过而立之年的蒋介石。
考察苏俄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
蒋介石是孙中山麾下重要的军事干部,这在朱执信遇害后显得尤为突出。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执信忽然殂逝,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吾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而过之。”十月革命爆发的那一年,蒋介石恰至而立之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迷茫中的中国革命青年以新的启示,走俄国人的路似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共识,蒋介石也就是在这时产生学习俄文,去俄罗斯学习的想法。1919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编》,这段时间,蒋介石尤为赞赏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称他们“意志坚定,精神紧张,久而不懈”,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因为列宁有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中国革命所缺少的就是列宁的“劳农兵制”。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制裁、封锁乃至捣乱,都未能动摇其国本。他认为这是因为“其内部之团结坚强,实力充足,乃有所恃而无恐耳。”对中国而言欧美乃至日本的外交支持都是靠不住,依靠地方军阀帮助革命更是荒诞不经,中国革命“恃有团结内部,放弃外交,以苏俄自强自立为师法”。他早就有意“赴俄考察政治,为彻底解决国是之计。”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派出代表参加会议。列宁抱病出席会议并接见出席会议的国共两党的代表张秋白和瞿秋白等,提出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议。孙中山在寻求西方列强援助无望的情况下,把目光投到了苏联。8月,孙中山决定正式向苏联求援。在此之前,蒋介石已向孙中山表白了自己的主张,并主动请求去苏俄考察。
蒋介石是个急性子,当他向孙中山提出赴俄考察时,恨不得马上就能批准成行。10月,孙中山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蒋介石为参谋长,可他到任不到一个月,就以经费难筹的理由,撂了挑子离开福州前线,回到溪口老家。孙中山知道蒋介石在闹情绪,这种情绪来自赴俄考察尚未成行,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兄前有志于西图,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矣,现大得其要领,然其中情形之复杂,事体之麻烦,恐较之福州情形当过百十倍。此无怪吾国之志士,乘兴而往彼都者,悉皆败兴而返。吾幸而得彼津梁,彼此可日为接近。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借,乃能有所措施。若毫无所凭借,则虽如吾国之青年共产党与彼主义完全相同矣,亦奚能为。所以彼都人士只有劝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者,职是故也。此可知非先得凭借不可,欲得凭借,则非恢复广东不可。此次广东一复,则西南必可统一,如是便可以西南数省为我凭借,则大有办法矣。……故兄前志之成否,则全在福州之一着也。”
这封长信可谓循循善诱,苦口婆心。信中所说:“我近日在沪,已代兄行之”,指的就是8月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第二次会谈,马林当面向孙中山建议,应让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对此亦有同感,赞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告诉蒋介石,中国革命“非先得凭借不可”,这个“凭借”就是西南的统一,只有完成这个“凭借”,才能实现蒋介石所说的“西图”之志,即赴俄考察,而联俄也才能“有所措施”。

1923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任命蒋介石为大元帅府行营参谋长,蒋介石因医治眼病,迟于4月到任,到任后又因军中关系不睦,于7月12日又“愤而辞职”,由香港回到溪口老家。当他得知孙中山将派代表赴苏俄考察时,立即动了心思,于7月13日在香港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写信,要求赴苏俄考察,甚至说:“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其态度的坚决已溢于字里行间,而意气用事的偏狭,又犯了“撂挑子”的老毛病。
广州成为革命的大本营,国民革命终于有了凭借。孙中山开始组团赴苏俄考察,考察的主要使命是学习苏俄的经验,以组建一支纪律严明的党军,也就是国民党指挥的军队。考察团命名为“孙逸仙博士考察团”,由蒋介石、王登云、符定一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组成,蒋介石为团长。8月5日,蒋介石来到上海,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党内元老张继、汪精卫等商组代表团等事宜。他还起草了一份给苏俄党政负责人的意见书,提出:“中国革命之根本计画,当在列强势力范围外之西北,得一根据地,训练有主义有精神之军队,备作革命军之中心势力,此为中国革命惟一方略也。”
苏俄党政军各方面都表示热烈的欢迎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率团由上海出发,经大连、长春、哈尔滨和满洲里,于9月2日到达莫斯科,他们受到苏俄外交官的迎接,开始了长达三个月的考察。
蒋介石本打算去拜见列宁,但由于列宁第三度脑溢血发作,虚弱不堪的病体已不能进行正常的活动而作罢。除了列宁外,他会见了苏俄党政军高层许多负责人,如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加里宁、齐契林、鲁祖塔克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他受到热情的接待,他后来也说:“对于我们代表的参观和考察,无论其党政军各方面,到处都表示热烈的欢迎,并恳切接待。”9月7日上午,蒋介石一行拜访苏联共产党中央机关,通过他们的介绍,他认为,革命前“在沙皇暴政统治之下,”“俄罗斯成了多种民族的监狱,……单是这种沙皇暴政就已经给予了俄共从事暴动,诡称革命,勃然兴起最有利的一个时代背景。”
他们象征性地出席一些会议,还是把重点放在了考察苏联红军和新式武器上。9月17日,他们参观苏军步兵第一四四团,这个团的党代表制度对他很有启发。党代表与军事长官权责分明。军事首长只负责军事指挥,党代表则负责政治教育和行政事务。党代表制度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他在黄埔军校就借鉴了这一制度,并一直沿用着。
他对苏联的武器开发尤感兴趣,在军用化学学校看到了毒瓦斯的使用和防御的研究。他对苏联正准备使用的骑兵用机关手枪,更是赞不绝口。这种武器轻便灵巧,每次可发射三十五颗子弹。他明显地观察到苏联对于武器的研究和开发,以及其武器的先进,已不在欧美各国之下。他还试乘飞机,那种感觉真是“翱翔天际如履平地。”
共产国际接待了蒋介石一行,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和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等听取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介绍。蒋介石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作了答谢辞,他说:“我们国民党专以三民主义作革命的旗帜,使大多数人民站在被压迫者一条线上,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是我们惟一的敌人。预料在两三年内,必定有一部分革命成功。我这次来到此地,对于我们中国革命,得到许多教训。不过各位对于中国革命的现在情形及实地工作,还多隔膜的地方;所以,我很希望国际友人多到中国去观察中国革命的现实,研究东方革命问题。”
蒋介石考察期间的言论引起共产国际的关注,甚至要发展他为共产党员。他要求苏俄予中国国民革命以援助,也得到积极的响应。当时被称为苏联“红军之父”、苏共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就一口应允这一请求,表示:“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
他在苏俄的许多谈话十分接近共产党的言论,有学者把这些概括成:“一、共产党是总理‘一脉相传’在‘国民党内’的命脉与血统;二、我蒋介石愿为‘国民革命’‘三民主义’‘共产主义’而死;三、‘直接’实行三民主义就是‘间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四、‘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而不相悖’;五、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中的一部’,世界革命不能无共产主义;六、‘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无纷争的必要;八、国民党共产党不可分,而应合;九、‘未有对共产主义以诚,而对三民主义不诚者也;’”等等。
这些坚定的左倾言论,很难让人相信是集一生反苏反共的蒋介石所言,如果因此而认为青年蒋介石是个共产主义者,或者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那都是冤枉了他。其实,他信仰的还是三民主义,只是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寻求西方援助无望的窘境之下,为寻求苏俄的援助而说出的一些应酬性的话语,很多往往又是言不由衷。
你们应该更多地研究自己的国家
蒋介石在苏俄所见所闻并非都是正面的信息,他就发现苏俄政府“轻信、迟缓、自满”。当他参观彼得格勒时,就觉得这个城市“精神颓唐,士气消沉。”他也注意到国有化造成集权过度,工厂缺乏有能力的管理者。他还认为苏俄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均分配。
领土问题更是导致他对苏俄的失望和不满。早在辛亥革命的那一年,沙俄就乘中国国内纷乱的局势,支持外蒙古独立。十月革命后的1919和1920年,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曾经两度发表宣言:“放弃帝俄时代有关中国的一切特权。”接着,1923年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又再次声明:苏联“绝无使外蒙脱离中国的意向。”可是一当接触到这些实质性问题时,会谈往往是“无结果而散”。
蒋介石在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会谈时,对所谓蒙古人怕中国人的说法予以反驳,他说:“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蒙古人惟其有怕的心理,所以急急要求离开怕的环境。在国民党正想把它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的目的时,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可苏俄的“诚意”不是外蒙自治,而是外蒙独立,这恰是蒋介石所极为不满的。
另一件事给他的刺激也很大,那就是10月10日,在他们下榻的宾馆举行中华民国国庆纪念会,莫斯科留学的中国学生几乎全部到场。这些年青的学生对苏联向有一颗朝圣般的虔诚的心,他们怀着好奇心,希望能听到更多的苏联的信息,可是,蒋介石却偏偏不向他们传递苏联的内容,甚至不无挑衅地说:“我不谈俄罗斯!……我要讲中国的情况。你们在如此热烈地讨论外国理论之前,应该更多地研究自己的国家。”
他还在讲话中介绍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年青的学生又不满意了,为什么不说马克思,为什么不说列宁,为什么不说俄国的经验。这些留学生当时就非难蒋介石,批评“蒋介石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有的还致信孙中山说:“中国革命党人忠臣多而同志少”。
这些不愉快并不影响他对苏联的兴趣,也不妨碍他对新的思想的探究。在莫斯科期间,他既读了《马克思学说概要》,又读了《共产党宣言》,读后还在日记中写道:“久久领略其味,不忍掩卷”。至于对苏联印象,虽不乏批评之处,但总体还是觉得“苏维埃政府对于人民已有相当基础”,而对苏联红军更是赞不绝口,称其“上下亲爱,出于自然,毫无专制气味”。“俄国武器研究及其进步可与欧美名国相竟,非若我国之窳败也。”
他在回国前与共产国际领导人话别时,表示“中国人民将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他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要想抵抗帝国主义就必须借助世界革命的力量。他甚至向共产国际建议,组成俄、德、中“三大国联盟来同世界资本主义势力作斗争。借助于德国人民的科学知识、中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该国农产品,我们将能轻而易举地取得世界革命的成功,我们将能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是12月15日抵达上海,给孙中山寄了一份“游俄报告书”,就急急赶回到溪口老家,一待就是两个星期。孙中山急欲知道苏联考察的详情,可蒋介石又耍起了小性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即,可他却连代表都不是。
1924年1月20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他既不是大会代表,就更别侈谈什么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而中共党员却多由当选者,这使他实在接受不了,愤愤不平的急躁情绪再也掩饰不住了,立即给孙中山去信抱怨道:“先生今日之于中正,其果深信乎?抑未深信乎?”3月14日,他在致廖仲恺的信中,这种情绪就更是暴露无遗,他说:
“尚有一言,欲直告于兄者,即对俄党问题是也。对此问题,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吾人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乃置事实于不顾。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孙先生惟有诋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惟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绝不信吾党可以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
他的所谓“直告”乃是真心话,在他看来不能因“其主义之可信”,而不顾苏俄“无诚意”、苏俄把中共看做“正统”、国共两党不可以“与之始终合作”的事实,也就是“应有事实与主义之别”,这也就埋下了四年后他与中共反目,血腥请党的伏笔。
我们所要效仿的是俄国的革命党
1924年5月3日,蒋介石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他的办校方式基本都是因袭苏俄的制度,这就是他所说的“主义之可信”。苏联教官教授军事课程,政治教官则多是共产党员。军校成立的国民党特别区党部,第一届区党部由五人组成,共产党员就有三人。第二届区党部由七人组成,除蒋介石外,都是共产党员。他特别看重党代表,说这是“救济中国军校的惟一的制度”,“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
黄埔军校在一年的时间内办了三期,成为拥有两千余名学员的军事实体,并直接参加了平定商团和东征之战,取得骄人的战绩。蒋介石也得以兼长洲要塞司令、东征军总司令。他亲手参加培植了军校教导团、军校学生军,在此基础上建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并任军长,国民党从此有了“党军”,而他本人也有了自己的嫡系,这一切都是“师法苏俄”的结果,也可谓“主义”的结晶。他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所要仿效的,是俄国的革命党。”“我们要党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他认为地主和富商是“我们最后的敌人”,社会的贫富不均就是由他们造成,“所以我们要革命”,“革命为全体人类求幸福,尤其是对于劳动阶级”,“打不倒乡下的地主,你们的敌人仍旧不能除去,你们仍旧要被人家压迫,没有出头的日子”。1925年4月9日,他在《主义不行党员之耻》中说,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明白地说,就是打倒资本家,反对大地主。这明明白白是为无产阶级而奋斗。……所以民生主义到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这些都是他在黄埔军校训话时,常常讲到的内容。
他与苏俄派来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军事顾问加仑都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加之苏俄给军校送来大批的武器弹药,事实已经证明了苏俄的援助,所以,他此时对来自诋毁苏俄的言论,大多予以抵制。12月11日,他在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举行的苏俄革命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本党不改组,苏俄同志不来指导我们革命的方法,恐怕国民革命军至今还不能发生。”针对所谓“中国人受俄国指挥”的言论,他理直气壮地批评:“我们且不讲我们是否已受了俄国人指挥,但我敢老实说,叫革命先进国苏俄来指导我们中国革命,我们世界革命的中国革命党员,实是愿意接受,而且是应该接受的。”
国共合作一开始就受到国民党内一些元老的反对,他基本没有附和,反而希望“国民党员应与共产党员携手对抗共同的敌人”。表示“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利害是完全相同,没有什么冲突的。”联合共产党,共同进行国民革命,“不是随便的事,自然另有眼光和主张的”。“总理认为现在的中国,除了共产党主张彻底革命,还可以同国民党合作之外,再没有第二个党派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了。而且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求进步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
在他看来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对于中国革命是至关重要的,应该“不分畛域,不生裂痕,终始生死”,而实行了三民主义,也就“间接以实行国际之共产主义也。”1926年1月1日,《民国日报》发表他的文章,最能体现他对于国共合作的真实的心态,他说:
“三民主义成功,与共产主义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者也。……未有中国之国民革命,而可不实行三民主义者也,亦未有今日之国际革命,而能遗忘共产主义者也。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之一部,而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矣。”
当西山会议派竭力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时,他及时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指出:“容纳共产党,此总理于本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而后毅然决定者也。自改组迄今两年,成绩俱在。……苏俄同志助成中国独立之国民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总理自信三民主义可垂之百世,推之世界,岂在中国国民革命尚未完成之时,而己惧于何种主义之蚕食,总理有如许伟大之自信力,逝世未一年,而后同志惴惴焉,惟被共产主义蚕食之是惧。其师大勇,其徒薄志弱行至此,亦可谓不肖之甚者矣。”
从1908年入同盟会,到1975年逝世,在几近七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的这段经历也仅几年的时光,而且是在矛盾和勉强中。他的联俄联共是有政治前提的,那就是国民党乃是正统,三民主义乃是惟一的理论基础,“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换句话说,有了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只是作为陪衬,因为,“三民主义可垂之百世”,是唯一的价值。反之,一旦这些受到批评和质疑,他的联俄联共也就不能继续存在和延伸,甚至会走向反面。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和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就是最有力的例证。
作者简介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这些文章中,多篇被文摘报刊和香港《文汇报》、美国《侨报》等报刊转载。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
瞿秋白纪念馆观后感